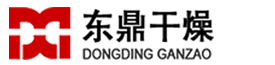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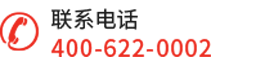

刘珩:detour折线正如一镜到底,改变了人对时空的理解,创造出多样的体验感和更多的可能性


verse编辑部:张江之尚是水泥厂改造项目,您最初接触场地的时候,对其有咋样的印象和想法?它们对于您后来的设计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珩:我记得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是一个细雨蒙蒙的阴天,场地上原有工业建筑尚未拆除,呈现出废墟状态。工业遗产和绿色植物相互交织营造出的沧桑感,会让人生出一种特别的冲动,行走在室内外的断壁残垣之间,我一激动就拍摄了许多照片,希望可以以此来留住这种动人心扉并让我震撼的场景和感受。
其中,筒仓的室内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着若能够将其保留并转变为新型空间,就能实现一种工业遗产的延续。后来,当再次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原有筒仓因为地下停车场的建设已被拆除。它其实涉及了一个工业遗产更新的典型问题,即如何在原址的有限场地内满足未来停车数量需求。在我看来,若没有筒仓,这将是个普通的生物科技园,因此我最初非常坚持保留筒仓。甲方考虑到我们对于筒仓的坚持,答应在拆除之后可以重建。于是,我们设计了和原有筒仓不太一样的重建的筒仓。


与安藤先生筒仓的设计手法不同,他的筒仓是被保留的,他对其做了减法。而我们的筒仓是被拆除的,我们对其做了加法,重建采用了一种混凝土和钢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重与轻的鲜明对比。对于重的混凝土,我们大家都希望它展现出不完整的样子,将其设计成剖面,而它又对着园区的主要道路,因此形成了能够将过去的工业痕迹展示给未来的立面。该设计手法可能是我们方案的最大特点。


verse编辑部:您最初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游牧方案,即现在的设计,另一个是洞天方案。游牧方案被张江之尚选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珩:我们的项目都是和甲方一起讨论之后定下最后方案。因为它是一个以办公为主的产业园,所以甲方希望办公的功能能够被最大化。
基于这个初衷,我们的设计随之不断调整,最后形成两个筒仓和规整的办公楼相搭配,实际上也是很实用的建筑。同时,我们也做了差异化处理,赋予重建的两个筒仓交通和公共空间的功能,以及标志性的彰显。这样三合一的效果,或许在未来能够方便项目的业态挑选和融合。

编辑部:您对张江之尚G地块南侧两栋建筑进行了再设计。G地块采用再现性织补的设计手法,您对于这一手法的理解是什么?是如何将其运用至具体设计里的?
刘珩:我们和张斌老师共同设计了G地块。致正的部分调整得更大,新的形式会更多一些。我比较怀旧,希望旧的形式,即工业感更强烈一点。旧有的工业化形式和未来的办公空间相结合,形成了“再现性的肌理织补”,这是非常明确的设计手法。
实际上,我们在类似这种旧改或城市更新项目里,大多数时候是采用“拼贴”这一突显时间性的并列手法,即历史和当代的并置。虽然这是一个重建项目,但也是一种历史形式的保留。对我而言,我更愿意用“拼贴”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设计手法。

编辑部:据悉,张斌老师邀请您一起设计G地块,致正负责窑尾塔和烟囱修复及北侧三栋研发楼,南沙原创负责南侧两栋研发楼。可否进一步谈一谈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加入张江之尚这个工业遗存改造项目的?您和张斌老师是怎么样做地块划分的?
刘珩:很谢谢张斌老师和孙继伟老师的邀请,我们才得以加入张江之尚。孙继伟老师希望我们也可以在致正的G地块里进行设计,张斌老师也非常民主地让我们挑选最有感觉的地方,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南侧两栋研发楼。虽然面积较小,但我们不在乎尺度大小的问题,因为我们对于筒仓特别有感觉,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分配了。其实,无论窑尾塔还是烟囱,都是G地块最有标志性的构筑物,也可以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建筑。在我看来,张斌老师做出了很好的设计。

编辑部:在您看来,工业遗存改造类型的项目带给建筑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此外,建筑师常常要考量哪几个方面?或者有哪些设计原则需要遵循?
刘珩:现场调研是工业遗存改造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先行操作。首先要了解场地的详细情况,其次是现状形式,之后做评估,比如哪些建筑会被保留,哪些建筑或许价值不大,以及对于甲方未来业态策划的适应性等。
评估之后,我们应该保留一些不可逆的形式。除此以外还有创新,它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超越工业遗产创造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这面临了较大挑战。例如,安藤先生的筒仓改造就是采用了“熟悉的陌生感”的设计手法。你能够正常的看到时间在那儿,但是又和之前的时间不一样,这一点让我十分钦佩,也是我们想追求的一种境界。


另一个是如何对旧有建筑进行保留,即如何修旧如旧并展现出一种原真性,这一点很重要。例如,建筑师马岩松的“万米仓”改造采用了很多修复手法,这就是尊重历史的一个表现,也是另一种挑战。虽然我们地块里没有这些被保留的历史建筑,但看到他们的项目将上面提及的点都结合进设计里,我也十分开心。


编辑部:整个张江之尚项目,旨在成为有活力、有特色、有趣味、着迷的可持续魅力城区,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提供满足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泛文化空间。您是如何将这个总的项目宗旨融入具体设计表达里的?此外,在功能和业态方面的布局,是如何考量的?
刘珩:我们收到的任务书是一个特定的研发楼,要求83%的利用率,所以设计里基本是五分之四为办公功能,五分之一为公共功能。我们营造了一个高效的中性办公环境,没有刻意加入某种状态,因此,整体空间突显简洁的风格和轻松的氛围。
圆筒区被注入较强的公共性,设计采取了比较有特色的新材料和颜色搭配,营造具有体验感的新空间,回应了生物科学技术领域办公族的诉求。与其他手法不同的是,我们在公共区域里设计了很多线路,让途经此地的人每次都能够尝试不同的线路到达自己的办公区。这种线路体验不是通常的两点一线,而是三点甚至四点一线,它能够准确的通过人们的诉求来改变,对于现在和未来也是一种多样的选择。我们大家都希望在这样一个朴素的办公空间里能够有一种多元性的考虑。

编辑部:您刚才说到折线,也曾经说过“折线帮助人改变了观察空间的角度,也改变了人对时空的理解”。可否谈一谈您的看法?您是如何将这一设计语言融入具体实践里的?
刘珩:我对于时间性的理解还是追寻当代科学和当代物理的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认为时间是相对的。实际上,空间和时间是对等的。我们在设计空间的时候,会希望可以改变人对于空间利用的体验,让他在不同的时段感受不同的体验。
我们切开筒仓形成向南朝东的剖面,随着阳光的变化,赋予其时间性,于是,人在不同的时段就能拥有不同的空间体验。例如,在红色桥上下穿行的时候,阴天和晴天形成的阴影分别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我们布置的植物在春夏秋冬也会呈现不同的景色。虽然身处同一个空间,但是人们会感受到不同时段的心情变化。因为这是一个半室外空间,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抽烟,又或者感悟某个人生真谛。在我看来,空间的变化可以为不同的人创造互动或偶遇的机会,这也是体验感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会有什么事发生,但是建筑师能做的是提供故事本身能够发生的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对于时间性的理解和实践。几乎每个项目都融入了这种体验感,我们叫做detour,即为空间注入detour,让一些平时不大有几率发生的事或许在此就发生了。
编辑部:在南沙原创的工业遗存改造项目里,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项目是哪两个?为什么?请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此外,它们与张江之尚项目相比较,设计手法分别有哪些不同之处?
刘珩:我们在2013年至2015年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比较多的工业遗存改造实践,大多分布在在深圳蛇口这个区域,后来就聚焦于城中村旧改。这些项目的设计手法和现在相比很不一样,这和当时国家规范比较放松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在旧房子里打桩,采用了在旧房子里长出新房子的手法,这是现今在深圳不太可能实现的做法。但在建筑师马岩松的“万米仓”改造里我看到了这样的做法,觉得蛮欣慰的。我们的浮法玻璃厂改造就是采用了从旧房子里面长出新房子的设计手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延续的手法,因为它在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方面会比较有机会一些。


大成面粉厂改造是一组公共建筑,我们尝试因地制宜,采取了让每栋房子都有不同空间的设计策略,在原有建筑本身的多样性上又迭代了另外一种多样性,这也是刚才提及的体验感的一部分。无论手法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都能够增加更多的空间体验感。这也代表着每一个空间都有各自不同的气质,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将其做得更加完整的一点。
我们过去的工业遗产改造,一定是有旧的,也有新的,这种旧与新的编织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近几年,我发现这样的存在越来越难了。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和国家规范、现行消防规范、逃生规范及结构的安全准则规范有很大关系,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退步,而不是一种进步。
编辑部:在建筑创作之余,您年年都会创作一两件艺术作品,参加1至2次艺术展览,去实践您的一些想法,让思维变得更活跃。可否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介绍一两件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艺术作品?
刘珩:前两年,我参加了坪山区和光明区两个区举办的一个和客家文化有关系的艺术展。当时,我们提取“麒麟”这一代表祥瑞的动物,采取一笔画的当代手法,用一条铁丝以折线的形式创造了它。这是一种一镜到底的尝试,它和我们的空间实践相一致,同时也利用了参数化这一新软件进行创作。
另一个是“2019深双宝安分展场改造‘地表的记忆’”景观装置。我们在地表上创作了一个放大的折纸。如何让手中柔软的小小折纸变成空间里巨大的硬质形态物体,我们对此思考并采用参数化扫描,将其变为5万点的定位,之后再精准放大几千几万倍,至210米长的放线,由此实现了这个装置。
它也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实践。将具有一定艺术形式感的物体和公共空间相结合,形成一个慢行系统,同时又复述了场地的原有历史——将水的历史转变为你们可以感知的公共空间,这对我们而言更加有意义。从思路诞生到最终落地只有三个月,它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但它的多样性体现出我们的不拘一格,而艺术本身就是凭着感觉做的。我们这几年也在尝试一种因地制宜的艺术创作。
编辑部:在建筑教育方面,您经验比较丰富,担任过多所著名院校的教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作为教师,您有哪些感受?这些任教经历给您的建筑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珩:一整天待在办公的地方做设计于我而言不太合适,而差异化的安排就好似alternative(切换)体验,被我视为一种休息的方式。将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项目,缩短到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就能完成的艺术创作,这是alternative的一种。
另一种是教学,它让我能够和年轻人交流,这十分有趣。他们的创作有时会带给我许多惊喜,在我看来,“For good or bad? It’s okay”(无论是好是坏,都不重要)。因为这种交流实现了alternative,激励了我们的实际创作,即有改变或者有交流才可能有进步。


编辑部:今年是南沙原创成立20周年,您当初成立事务所的初心是什么?从现在回望这二十年,是不是已经达成了当时的初心?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此外,面对当前行业放缓的大环境,南沙原创是怎么样应对的?
刘珩:坦白来说,时间的流逝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多年来,我们始终秉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坚守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所创造的作品必须是我们自己比较满意且能够有所贡献的样子,而实际却并不理想。在我看来,人们历经20年应该是在慢慢的提升。但对我们事务所而言,时间带来的积累似乎还未达到一种能转换升华的状态。我们依然艰苦努力,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
国家在这2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筑业亦如此。建筑业实际上一直与经济大背景共存共荣,而西方经验也在某一些程度上呈现给我们这样的事实。回顾过去,我希望自己能更加轻松一些,或者社会能更尊重建筑师的付出,让我们也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和思考上。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更有利的方向,也是文明发展的最好方向。
但从目前来看,社会对于专业的尊重度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让我不禁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行业的放缓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大家可以加强研究和开发,可以把一些原本被压缩的日程回归到正常范围来慢慢琢磨,最终创造出更加讲究和精致的作品。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把握好这个机会,未来可能仍然是你的。只要你时刻准备着,这可能就是我的态度。

刘珩:建筑具有一个类似集团军作战的属性,它是一个团队的努力而非一个人的工作,当项目落地时,支持建筑师的是一个庞大的施工队伍。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行业上下游对于建筑的品质、标准和付出没有达成共识,仅凭建筑师的热情,就如同堂吉诃德一般,一个人的呐喊很难成事。
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感激张江之尚项目。他们与长三角的许多甲方一样,都拥有很优秀的品质,对质量特别认真,对每一个细节很看重。无论是材料的选择,还是与建筑师的合作,他们都能挑选出最合适的材料和样板。他们非常正规且专业,会不顾一切代价确保能够按照1:1的比例实现放样。在珠三角,很少有甲方及其管理标准能达到这种水平。
在这个项目里,我感到特别欣慰。在这种集团军式的工作中,如果每个协调部门的人都与你有共识,即都有共同的质量发展要求,你会发现工作会轻松很多。因此,只要任何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最终的结果自然不会差。这也是我对于张江之尚项目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而这些期望也确实正在实现。
我希望它可成为我们国内新一轮产业园空间发展的标杆。我认为标杆应该具有多样性,包括保留、新建以及半保留半新建的并存可能性,这样它就能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我相信最终,它将成为一个高质量的产业园。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设计宇宙大奖旨在表彰对设计产业有卓越贡献的设计机构、品牌/企业和极具影响力的大事件。
《编码物候》展览开幕 北京时代美术馆以科学艺术解读数字与生物交织的宇宙节律
Apple Watch电池膨胀集体诉讼案完结 用户可获得20至50美元不等的赔偿
英特尔确认下半年开发Panther Lake 次年是Nova Lake 取消Falcon Shores
《编码物候》展览开幕 北京时代美术馆以科学艺术解读数字与生物交织的宇宙节律